前几天找资料的时候,发现了雄文一篇,《What If Friendship, Not Marriage, Was at the Center of Life?》,看到这个标题就很想看,读完之后,觉得太喜欢了,于是花了四天时间翻译了一下。
生活中有很多密友、无性爱的夫妻、同性情侣、最近还有人跟我提出让我加入他们的多变关系……所有对“友谊”和“爱情”有困惑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篇文章,虽然在讲友谊,但是实际上,文章在探讨新型的关系,而这种关系,其实几个世纪前就被人玩过了,而最近又回潮,开始挑战社会准则而已。
这篇文章我最喜欢的地方,一是讨论了性和爱的关系,隐藏在对“友谊”和“爱情”的讨论里,二是其中一个基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很多人在爱情中犯的一个错误,“约翰说,这种爱情就是‘一站式购物’。情感支持、性满足、共同的兴趣爱好、智力上的相互帮助、抚养子女的相似理念,人们往往想把这些全部放进同一个购物车里。他认为这简直就是不可能。”
另外一个收获就是发现了《大西洋月刊(The Atlantic)》这个宝藏。我一直以为《大西洋月刊》是个科学类读物(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个偏见),没想到居然是文化类读本。而这篇雄文是今年10月20日发表在《大西洋月刊》上的,点进去一看,居然有个“友谊文档“:
插图和文章都很精品,和《纽约客》的口味比较像,但是更偏文化类。喜欢的旁友们可以定期读了。
话不多说,以下是正文。
如果友谊取代婚姻,成为生活的核心
卡米·韦斯特和她的现男友约会几个星期的时候,她告诉他,他的级别比她的闺蜜要低。韦斯特每天都会和凯特·迪罗森开着免提打电话,她知道,她的男朋友会听到个几句只言片语。但是她也知道,就像其他的约会对象一样,这个男朋友并没有了解到她们友谊的本质。韦斯特对他说:“我必须让你明白,她哪儿也不去,她才是我的No. 1。”迪罗森的位置比他高,而且,韦斯特告诉他:“(当我有困难的时候),你出现,她也会立即出现。如果你在这个情况下认为,她不是我的No.1,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。”
韦斯特如此坦率,是因为她下定决心不想再重复她二十四五岁时的那些沮丧经历。她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察觉出来了他并不是她的第一位。他试图让韦斯特远离迪罗森,他骂迪罗森是个贱货,给韦斯特带来了不好的影响。韦斯特31岁的时候和他分手了,她下定决心再也不让任何男人给她的友谊施加压力,反之亦然。
韦斯特和迪罗森明白这个约定的意义。韦斯特告诉我:“理所当然,我们的男朋友,我们的另一半,我们的丈夫,应该是我们的No.1。但在我和迪罗森这里,不是这样的。”
过去几十年里,美国人对“合法的浪漫关系”有了更宽泛的认知。法庭现在可以给同性情侣颁发结婚证,美国人更愿意晚婚,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和别人同居,而不是和伴侣去领证。不过,不管这些变化如何如何,有一件事没变:我们对一夫一妻制下的浪漫关系的期待,始终是行星,而其他的关系则是卫星,必须围着这颗行星转。
像韦斯特和迪罗森,把友谊放在生活的核心位置的话,这个规则就被打破了。她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显然侵犯了爱情的领地了:她们一起居住,一起购物,帮对方带宝宝,使用联名信用卡,使用对方的医疗保险,在涉及各种法律问题上,她们相互给对方开授权书。除了性爱,这种友谊几乎拥有了爱情关系里的所有要素了。
尽管这样的友谊如此夯实亲密,但是它不属于任何一种清晰明确的归类。它看起来像“闺蜜”,但是处于这种关系里的人觉得“闺蜜”可是够不上的。我们只能在汪洋大海里寻找类比。有人把这种关系比成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,而另外一些人则看作是爱情了。罗格斯大学的教授布莱尼库伯 (Brittney Cooper) 在她的新书《雄辩的愤怒 (Eloquent Rage)》里说:“有人考量着如何去爱你,为你挺身而出,同时又有一种灵魂伴侣的姿态,这种关系就是爱情了。”
而另外一些人则觉得这种关系在亲人和爱人之间。乔里维拉和约翰卡洛在得克萨斯的奥斯汀的一家gay吧里认识的。里维拉当时在主持脱衣舞大赛,卡洛在这个比赛里赢了250刀,那一夜之后,两人感觉就像“兄弟”。“兄弟会想要一起出去玩,为彼此付出吧。”卡洛这么说。当他考量他们之间的同居生活的时候,他告诉我说:“我们有点点像一对结婚了的情侣,虽然我们没有结婚。”他把他们的关系看成“兄弟”又看成“夫夫”,这或许表明,婚姻和兄弟情都不能准确描述他们的友谊的精髓。
对于亲密的友谊,这个社会并没有一个剧本来描述这样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,应该如何发展。这种关系是量身定制的。米亚普利多是德鲁大学的学生,今年20岁。她说她和她的“灵魂伴侣”,同样是20岁的塞维亚索察吉,为她们的关系一起铺路,一路走来,她的感受就像在“创造科学怪人”:她们俩都阅读了很多关于几个世纪前的女性关系的故事,但是她们为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代关系探索出来一个框架。她们发现她们在性格上互补,就像大侦探福尔摩斯和他的助手华生一样。她们对彼此偶尔产生一些情愫,那是又一次普利多在一个车库大卖场里买了一本二手书,书里面夹着一张纸条,纸条是一个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情话,他们亲切地称对方为“小泡泡”和“臭粑粑”,自此之后,她们俩也就这样相互称呼。普利多觉得,在索察吉和她自己的需求和欲望上去建立关系,会更加无拘无束。她觉得,社会告诉你某种特定关系一定要有这样那样的要素,但是这是一个泥潭,而她和索察吉的关系却不会陷入这样的泥潭。
很多把友谊放在生活中心的人都会发现,其他人对这种关系的重要性不太理解。作为一个社会整体,我们是有能力拓宽我们所理解的亲密感和关爱感的,而他们的这种友谊可以在此成为标杆。
迪罗森和韦斯特18岁的时候刚认识的时候,她们也并没有想要挑战一下友谊的基本规范。她俩在北卡州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新兵训练营里,循规蹈矩地说着“是的,长官!”喊到对方的时候,还必须在她的姓氏前面加上“新兵”俩字。夜晚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时光,新兵迪罗森和新兵韦斯特几乎都是在她们的上下铺前谈天说地。闲聊中,她们发现韦斯特的母亲刚刚搬到了新的住处,这个地方离迪罗森的老家俄克拉何马州的塔尔萨城开车只有20分钟。迪罗森和韦斯特在新兵训练营的一个月的休息期间也呆在一起,她们开着韦斯特妈妈的黑色小轿车在塔尔萨郊区兜风,听着rap,摇下车窗。接下来的四年里,她们被分配在相隔千里的地方,期间迪罗森还被派遣去了伊拉克。自此之后,她们相互陪伴对方,受伤、工作烦恼、感情问题。她们的感情真正开花结果的时候是她们从塔尔萨的社区大学毕业,自此之后她们几乎每天都一起度过。那个时候,迪罗森正在等着她的离婚文件被公证,而韦斯特已经是个三岁的科迪的单亲妈妈了。
韦斯特找到了一个在酒吧的工作,白天要补觉的时候,迪罗森就帮她带科迪。迪罗森也经常和韦斯特一起去学校接送孩子。当两个女人一起走在学校的走廊,穿过学生们的储物柜的时候,韦斯特说:“就跟翻江倒海一样。”迪罗森感觉到其他家长在打量她。时不时的,有老师会悄悄地走到她们跟前,看着迪罗森问她:“这是谁?”“人们总是问我们怎么认识的,或者问,你们俩是姐妹吗?更多时候很多人会以为我们俩在约会。”31岁的迪罗森这么说。而跟这些好事儿的人解释她们复杂的友谊,韦斯特和迪罗森会都觉得太麻烦。
词汇表里没有任何词条来刻画韦斯特和迪罗森之间的关系,像她们这样的人就从描述友谊的语言里找出只言片语,零零碎碎的词语来形容她们自己。她们会说她们像“灵魂伴侣”“柏拉图式的生活伴侣”“我的人”“死里逃生的小妞”“同性柏拉图伴侣”“大友谊”。对于另一些人来说,这些名词的作用就是在搭配“友谊”这条漂亮的项链,指的就是在“友谊”的帽子下的两个人。其他人,比如韦斯特和迪罗森,会找一些对其他人来说更简单易懂的词汇。她们俩意识到,其他人明白新兵训练营是一个紧张的环境,这个环境下可以滋生同样紧密的友谊。她们俩对其他人说她们是“新兵训练营里的闺蜜”,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就没什么疑惑了。
过去十多年里,妮可桑德曼并不介意,只有她自己和瑞秋赫博涅明白她们俩之间的关系。桑德曼总结说她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像是“不想亲吻对方的生命伴侣”。
她们一起在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城一起居住的时候,双方就对彼此的语言和生理变化了如指掌了。在赫博涅怀疑她怀孕之前,桑德曼逼她买了试孕棒,带着她走进洗手间,然后坐在旁边等着她做测试。四年之后,两个人的角色互换了:赫博涅对桑德曼也有同样精准的预感。“我们对彼此的关注简直比对我们自己还多。”37岁的桑德曼告诉我。
人们对她们的关系产生困惑或者敌意的时候,她们偶尔会解释一下。她们对彼此的昵称是“老婆”,桑德曼当时的丈夫对此毫无异议。但是当赫博涅和她的丈夫离婚,重新开始约会的时候,她的约会对象吃醋了,尤其是和她约会的女人们,她们的醋意更加明显。为了平息她们的怒火,桑德曼只好勉强把“老婆”这个称呼改成了“老波”。
离开阿拉斯加之后,俩人在不同的时区住过几年。桑德曼和她当时的丈夫因为他的工作来回搬家,最终她搬回了阿拉斯加,而赫博涅搬到了印第安纳州。她们的精神支柱就是打电话和偶尔见面。桑德曼说赫博涅生活遇到难处之后,和她的交流就越来越少了。当时她被恋人施暴,因为工作的时候没人照顾她女儿,所以她的工作也丢了。她非常沮丧,2018年十月,她自杀了。
赫博涅的死让桑德曼极为悲痛。她们俩都幻想过一起搬到阿拉斯加,住在她们相遇的地方的附近,赫博涅也十分想回来。现在这一切都化为泡影。赫博涅去世的六个月里,桑德曼去超市都戴着耳机。她根本不能忍受和别人闲聊。
桑德曼发现她很难和外人描述她的悲痛。“大多数人无法理解。他们会说:‘啊,是啊,我也有个高中的朋友去世了’,或者跟我说一些类似的。但是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共鸣。”而其他的一些人就会把她的故事线里添加一点淫秽了,这么一来他们才能理解。桑德曼说,因为赫博涅是双性恋,很多人以为她们其实是恋人,而且还以为桑德曼不愿意出柜。
莱斯大学的哲学教授伊丽莎白布雷克 (Elizabeth Brake) 的研究主要是婚姻、爱和性。对她来说,桑德曼的经历是个悲剧,并且极其不公平。因为友谊并不会得到法律的保护,法律有个准则:和爱情相比,友谊没有那么珍贵。很多人争辩,彼此忠诚的友谊也需要法律的认可,但是在法律的这个准则下,这些争辩就站不住脚了。但是如果,比如说,法律把丧失亲人的条款扩大到朋友的范畴,布雷克坚信我们在悼念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社会期待。人们或许会明白,对于桑德曼来说,失去赫博涅无异于失去了爱人。
法律上的优惠和社会标准都不站在她这一边。但是桑德曼感到那些有亲密友谊的人能够更理解她。桑德曼说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。两个小时的时间里,他和桑德曼坐在车里,发动机熄了火,车停在超市的停车场。她对他说赫博涅的点点滴滴,然后泪如雨下。她的朋友说:“听起来她伤了你的心。”桑德曼告诉我:“那是第一次有人理解我。”
亲密的友谊并不是一直都让人摸不着头脑无法定义。18世纪至20世纪初是同性亲密友谊的黄金时期,这种关系被称为“浪漫的友谊(romantic friendships)”。美国和欧洲女性没有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,但是她们之间相互通信的称呼都是“我的爱”“我的女王”。女性们之间相互传阅和朋友的照片集,在空白页里写满了浪漫的诗句。在埃米·玛蒂尔达·卡西 (Amy Matilda Cassey)的友谊相册里,她的好友,废奴主义者玛格丽塔·福滕 (Margaretta Forten)摘抄了一首诗歌的一小段。最后几句这么写:“美好的友谊连接着天国,因为天堂和友谊有同样的面孔。”作家们描写着“浪漫的朋友”之间发生的各种故事。1897年出版的小说《黛安娜薇翠丝(Diana Victrix)》里,有个角色,恩伊德,她拒绝了一个男人的求婚,因为她最好的女性朋友已经占据了她生活的全部,所以她没法留出任何空间给那些追求者了。这简直就是卡米·韦斯特的前世:恩伊德告诉这个男人,如果他们结婚:“你本该可以第一个来的,但是你不能,因为她是第一个。”
原文来自:没有围墙的世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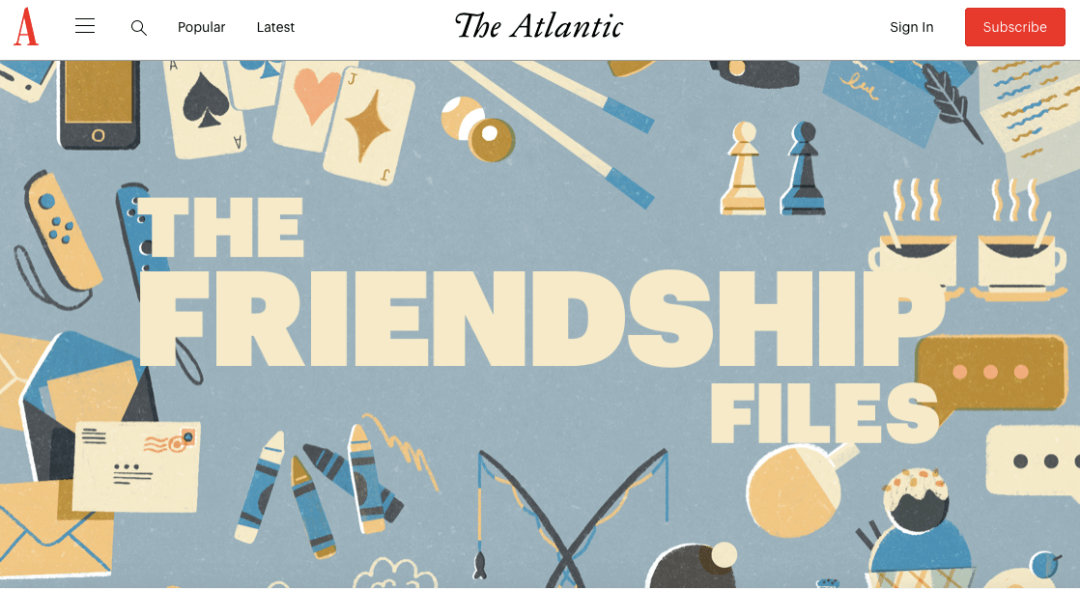







不以稳定性生活、同居关系为中心的关系,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法律如何保护的问题。但转念一想,可能正因为不在法律的优惠政策林,这样的关系才显得动机单纯。